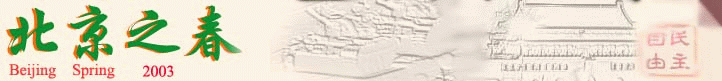荆棘桂冠
秋潇雨兰
那是一九八三年五月,我是贵州大学中文系八二级的学生,进校不到一年,
具有一颗热情似火的心,然而又时常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乐於助人,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共青团团员,各方面都合乎党的好学生的“标准”
,可进校不久,我曾经要求退学。因为一贯成绩优秀的我高考没有考出应有的水平
,只被一所普通大学录取,辜负了老师和父母的厚望,本来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在高考之前紧张的复习阶段,家里由於父亲转业回北方老家工作,妈妈和外婆均不
乐意,整日吵吵闹闹,我心烦,鬼使神差地“不幸”迷上了文学,几乎没用功复习
,弄虚作假,桌上摆的是课本,抽屉里藏的是小说,哄了父母害了自己。我相信自
己一定考得起,不过考不起外省的大学了。不久,父亲和弟弟回河南郑州了,外婆
也去了舅舅家,哥哥考取遵义体校走了,剩下妈妈和我。考完试以後,我有点心虚
,觉得对不起妈妈,所以预先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告诉她我是一定考得起的,只不
过考不起外省的学校,如果通知书来了她要埋怨我的话,我就退学,跟她回郑州去
补习再考。果然贵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以後妈妈和老师均很失望,我比
较难过,想申请退学,可妈妈又坚决不同意,不久,她把我送贵州大学就回郑州去
了,我一个人在贵州很孤独。进校以後,由於对各方面都比较失望,加上一些阴阳
怪气的同学惹我生气,於是我就提出退学,老师没同意,因为老师们喜欢我,器重
我。後来,我一头扎进书本里,看开了,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其实,这一切都是命
运的安排,它最终要把我推到黄翔身边去。所以生活中许多阴差阳错的偶然,实质
上是命运的必然。
在迎新生进校时对我很好的两位男生是中文系八一级的学生,喜欢写诗,曾
经参与办《崛起的一代》,所以刚进校他们就非常自豪地给我介绍了这份曾轰动一
时的大学生刊物,不过他们没有介绍黄翔。不久,他们介绍我读了《约翰·克利斯
朵夫》和泰戈尔的许多伤作品,这些书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某种升华。各个年级差
不多都有诗社,我们年级也成立了,我是诗社的一员。八三年五月,一次全国性的
诗会在贵州的历史名城遵义市召开,我们诗社获准前去旁听。已经成名了的诗人北
岛、杨炼、顾城、王小妮、徐国静等等都出席了这次诗会,顾城的未婚妻谢烨也去
了,那时,我不知道她也写诗,她把黑油油的长辫子盘在头上,皮肤白里透红,我
觉得她很朴素,也很漂亮。(多年以後,我为她死得那么惨,而且是死在顾城手下
常常异常痛心。)王小妮很瘦,看上去比较柔弱,但很精干。徐国静给人的感觉为
文静、善良、真诚,她非常欣赏北岛的冷峻,谈起贵州高原来一往情深。我感觉高
原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强烈地吸引她。她常常一个人默默地散步,在许多女孩中她
很喜欢我,而我也喜欢她这位亲切的大姐姐。认识黄翔以後,我才知道她来遵义以
前专门找到张嘉彦请他带她去拜访黄翔,因为她给《崛起的一代》投过稿,所以和
张嘉彦有联系。黄翔和他的作品深深震撼了她。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她在送
给黄翔的笔记本上题了这样的话:
“黄翔:
一个灵魂在痛苦中冥冥的飘飞,许多许多心被感召了,於是,才有穿过山峦
与波涛的人来寻找。
徐国静”
八六年夏天,我和黄翔去北京,第一次见面她就微笑着说:“黄翔写信告诉
我与他结婚的女孩和我在遵义诗会上见过面,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猜就是你。”
北岛确实很冷峻,那时,他给人的感觉比较忧郁,甚至有点阴沉,杨炼则洒
脱不羁,热情洋溢,顾城圆圆胖胖的象个大男孩,有着一双朦朦胧胧、似醒非醒的
大眼睛,单纯而又迷惘。黄翔对北岛、杨炼、顾城来贵州没去看他有点耿耿於怀,他
说搞民主墙的时候和他们都很熟,那时他们还没成名,顾城见到他时张开双臂给了
他一个大拥抱,激动地说:“《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火神交响诗》之一。
作者注)简直是中国的惠特曼!”不久顾城和杨炼约好在前门等他,他因忙失约了
,後来顾城寄信给他说:“我们像等侯英雄似的在前门等了你两个钟头。”北岛由
於是《今天》的主编,所以黄翔与他们打的交道要多些,北岛曾经帮助“启蒙社”
十元钱(那时十元钱很值钱),黄翔一直记在心上,他觉得北岛人好、城府很深。
他说杨炼很喜欢他的《火神交响诗》,《今天》在北师大举行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
,杨炼还递给他几行诗请他看看,不久杨炼发表了一组《金芦笙交响诗》,看得出
《火神交响诗》对他的影响,他认为杨炼从那以後进步很快,确实很有才华。八六
年夏天黄翔和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见到诗评家谢冕教授时,他说杨炼曾经异常兴奋
地跑来告诉他黄翔的《火神交响诗》写得棒极了!我感觉,已经英雄落难的黄翔内
心深处其实很希望这些昔日的友人来看他,这对异常孤独、寂寞、并被排斥在文坛
之外、身陷逆境的他来说是一种安慰,可他们没有来,他很失望,不过也能理解他
们。这些已经成名的朦胧诗人曾经也是《崛起的一代》的撰稿者,这份大学生刊物
发表了他们许多作品,对扩大他们的影响起过作用。张嘉彦和一位他原来的同班同
学,《崛起的一代》的活跃分子G也参加了这次诗会。张嘉彦穿着一件肥大的土黄
色的中山装,後来我发现黄翔也有一件相同的,张的这件还是黄翔送他的哩,由於
他是我们的校友,又曾经是《崛起的一代》的主编,加上稳重健谈,不象他的同学
老是想追我们诗社的女孩,故赢得了我们诗社成员的尊敬。在诗会之外我们还自发
组织的一次晚间聚会上,大家请他朗诵和谈谈诗歌。他站起来,很有激情地朗诵了
一首短诗: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粱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
一九六八年
这就是黄翔早期的诗篇《野兽》。这首诗深深震撼了在场的人,大学说,在
那个可怕的年代,中国居然有敢写这种诗的诗人?!说句良心话,这个名人汇聚的
诗会有点令人失望,诗人们的演讲缺乏激情和深度,尤其是一些老家伙们的发言更
让人觉得乏味,所以张嘉彦朗诵的这首诗仿佛是一针兴奋剂,令人振奋。紧接着张
嘉彦给大家介绍这首诗的作者,他怀着崇敬之情告诉大学,这位诗人把一生都奉献
给了诗歌,然而由於他的叛逆性和抗争性不为官方理解和宽容,作品得不到发表,
受尽迫害,历经苦难仍然不改初衷,坚持写作……听了张嘉彦的介绍,大家才恍然
大悟,这个诗人原来就是诗会上有位老诗人严加痛斥的向诗坛泰斗艾青挑战的那位
“太狂妄”的诗人,大家很吃惊,原来我们贵州隐藏着这么一位惊世骇俗的诗人,
怎么原来一直没听说呢?不知为什么,刹那间,我的心里情不自禁地萌生一个念头
,我想,将来如果我遇到这位苦难深重的诗人的话,我一定会爱他并帮助他的。这
个念头是那么神圣,不含一点世俗的男女之爱,它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从
小别人就说我有一付菩萨心肠,那些受苦受难的英雄人物一直是我心中的爱情偶像
,我这个连自己都拯救不了的小女孩老爱幻想着去拯救他们。现在,也许又是这种
幻想在作怪吧。我不知道别的听众有什么反应,环顾四周,发现一些人在认真倾听
,然而表情捉摸不透,一些人的好奇劲过去,躲到别处去谈悄悄话了。张嘉彦谈完
以後,大家开始自由交谈,我走过去坐到他的旁边,继续当他的听众,带着浓厚的
兴趣请他接着谈谈那位诗人……那晚,他还介绍了黄翔的老朋友,默默写作很多年
的贵州诗人哑默……後来,我在黄翔家第一眼见到张嘉彦是他给我开门时,表情很
庄重,似乎知道开门迎接的客人就是我,他仍然穿着那件肥大的土黄色的中山装,
进去以後,他笑着对我说:“我一来黄翔就异常兴奋地告诉我,最近生活中发生了
一件大事,他爱上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并且我和那位女孩在遵义诗会上见过面
,我一猜可能就是你,今天一看,果然如此!”我羞得满脸通红,含笑不语。介入
黄翔的生活以後,诗人哑默和评论家张嘉彦均成了我的朋友,尽管在黄翔第五次入
狱的那三年我们的友情一度中断,但黄翔出狱以後这股断了的友情之绳又接上了,
大家和好如初。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互相谅解、彼此宽容、肝胆相照,哪里会有那
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呵!
那晚聚会之後的第二天,我们这伙贵州大学的诗歌爱好者又随女诗人董佳佳
去到遵义师专的老师徐泽荣处,他是张嘉彦的朋友,曾经也是《崛起一代》的活跃
分子,那天我不太合群,不想参与大家的闲聊,一个人坐在书桌旁默默不语,徐过
来和我说话,我问他有没有《崛起的一代》?我想看,他拉开抽屉,我一眼就看见
放在最上面的一本油印刊物《启蒙》,我很惊喜,对徐说要看这本,因为昨晚张嘉
彦谈到这份刊物。徐泽荣叫我不要声张,悄悄看,免得其他人注意,因为这是禁刊
。我躲到一个角落,捧着这份刊物静静读起来。翻开发黄的封面,一股浓浓的油墨
香味扑鼻而来,读完“启蒙宣言”,深为震动,再接着读《火神交响诗》……我的
五脏六腑都被一种精神的雷电击毁了,灵魂刹那间燃起一场熊熊大火,生命在烈火
中焚烧、惊呼。某一瞬间我似乎失去别的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火!火!火!
这片火与我记忆中的一片火汇合,我看见高考前的我有个夜晚在灯光下读郭沫若的
《凤凰涅磐》,那是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是在一本杂志上无意中翻到的。那时,我
还不能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赏诗歌的好坏,读诗全凭直觉。诗读完了,凤凰在
火中涅磐,那使凤凰涅磐的火似乎烧着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我放
下书,走到後阳台上吹吹夜风,举目望去,浩瀚的星空下,农人们正在收割过的宽
阔的田野上燃烧大堆大堆的油菜杆,火光直冲云宵,映红了眼前一片黑夜。我被这
壮丽的景色迷住了,忘记一切,心似乎听见了火的召唤,它召唤我象凤凰那样勇敢
地跳入火中燃烧,经受灵魂的洗礼,在火中升华,在火中涅磐和再生……我站在阳
台上,热血沸腾,全身融化,如入梦幻之境……最後,火光消失了,那些成堆的灰
烬将以另一种生命的形态渗入大地,然而,那火的召唤却没有消失,它隐入了我生
命的深处……今天,我的灵魂又被一片无边无际的火弥漫,这是精神之火,它来势
凶猛,无坚不摧,那隐伏在我生命深处的火的召唤再一次响起,它的声音越来越深
沉,越来越嘹亮,越来越庄严和雄壮,随着这个神秘的召唤,灵魂义无反顾地跳入
这场烈火中,不惜将自己化为灰烬。我获得“涅磐”和“再生”了的第一个感觉就
是,以往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欺骗人的教育。我的脑海里浮现初中时代的一个情景,
校长威严地站在台上,从他那张阔嘴里发出一种义愤填膺的声音:“……前些日子
国内有一股反革命势力很嚣张……‘启蒙社’是最大的反革命组织……启蒙运动是
一场用心险恶的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分子魏京生被处以十五年徒刑,罪有应得…
…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出卖国家反对党,妄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台下,无数
年轻的脸庞怀着“阶级仇民族恨”认真倾听着,鸦雀无声……
今天,我这位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由於读了手
里这本发黄的“反革命刊物”突然间顿悟了,因为我认识到的一切根本不是什么“
反革命”,而是真正赤诚爱国,真正的忧国忧民。
我的清醒导致我更加忧郁了……
八三年五月三十号,是偶然也是必然,我认识了黄翔,在灵魂深处,我们一
见衷情,然而,那爱似乎跋涉了无数个世纪,等待了几千年才最终到来。
认识他不久,他就送我一个名字:
“雨兰”。
他说,我忧郁的神态就象雨中的兰花。
许久以後,我终於明白,我冥冥中听见的那种神秘的火的召唤其实是命运的
召唤,因为黄翔这个人和火有很大关系,他出生的时候整条街失火,他开蒙读书的
小学叫火神庙小学,他的成熟的处女作是《火炬之歌》,他搞启蒙运动在北京落脚
的第一处叫火神庙,他第一次震惊中外的诗篇叫《火神交响诗》……他名字的五格
——天格、地格、人格、外格、总格全为五行中的“火”……
这不是命运的启示又是什么呢?
我要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了,命运对他也有某种暗示。
那段时间,他正在创作变体诗《“弱”的肖像》,其中,写於一九八二年十
月十五日的《最初的暗示》和写於十七日夜的那首《黑太阳》能够看出这种暗示,
我进大学有一个多月了,十五号我刚满十七岁,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少女了,满十七
岁的那天我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所左右,夜晚,我一个人呆在
空空的教室里狂热地写诗,渴望一种灵魂和精神的飞升……我本出生在贵阳,童年
时和亲爱的外婆外公就生活在这座城市,也许我与他常常擦肩而过也说不定呢?我
的父亲从北方参军,南下到贵阳,又到遵义,最後到余庆,我上学以後回到在余庆
工作的父母身边,在那座寂寞而又偏僻的被群山环绕的小县城一呆就是十年,现在
我又回到贵阳,和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两个人的生命磁场越离越近了……
十月十五号,也即我生日的那天,他写了《最初的暗示》:
“一棵树在二月里出现了。
象这样的树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呢?
但我的感觉里只有这么一棵树。
它从车窗外一掠而逝;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引起你的注意就退出了你的视线。
它伫立在一个小土岗上;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的平平静静的土岗。
‘带我走’远空和群山中传来一声模模糊糊的叫喊。
我掉过头去。
仿佛在那儿,在那不能移动的小土岗上,沙沙响动地伫立着热情的寂寞。”
不知为什么,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我就感觉自己是那棵伫立在平平静
静的小土岗上的热情而又寂寞的树,是我在远空和群山中呼唤他——“带我走!”
十月十七日夜晚,他情不自禁地写了《黑太阳》,那时,他异常衰老和绝望
,他甚至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然而,他又在苦苦地期盼着什么……
“我被我的老年抛在临终的路口。
松软的昏暗在我的背後凹陷下去。我的凸出的脸像未愈的伤疤。
我坐在路口,仿佛在等候什么人……”
“坐久了,我斜拄着拐杖立起身来。
我一无所有,只有背着的‘空无’。
‘老爷爷,您好!’
一轮蓝黑色的太阳旋动着我。
美丽。巨大。微凉。
我突然感觉,倾泻而下的光的尽头的深不可测的黑暗。太阳光是黑色的。
‘您老啦,我回来了。’
我听出这是我心爱的那个十六岁的少女的声音,它仿佛藏在太阳黑色的光芒里。
我在龟裂的微笑里默默无语。
我不敢朝前看,也不敢朝後看。
云霞。爱情。青春。蘑菇般丛生的记忆。我没有从我的往事里采撷下什么。
我背着‘空无’的行囊移动在昏黑暮年的布景中。在垂死的路口执著地等候着一
个一直不肯
出现的人。”
不久,他执著地等候着的一个一直不肯出现的人终於出现了,并且接过他的
行囊和他相依为命,一起在风雨和泥泞中朝前行走……
办民刊《崛起的一代》,由於不是黄翔出面,所以这一次他没有遭殃。他的
健康垮了,整个人虚弱不堪,有一种死亡之感,然而,在这种可怕状态中,他却丰
富和发展了他的情绪哲学。在他称为“停尸房”的小书记里,几乎是长期躺在单人
床上,他支撑着完成了重要作品之一《“弱”的肖像》,在前言中,他写道:
世界范围的情绪“诗”学的黄金时代尚未到来或正在开始。
人生情绪的“经历”:“在海德格尔那里,是走向死亡的经验;在雅斯贝尔
斯那里,是在‘边缘状态’或‘临界状态’的遭遇;在萨特那里,是人感到‘厌恶
’或‘呕吐’;在马尔赛那里,是走向神秘的经历”;
而在我——一个东方人黄翔这里,是以“诗”囊括上述抽象地展开在“哲学
”形式中的“普遍”的人生“经历”又始终在“诗”中“情绪地凸现”“颤栗”和
“逃窜”在“死”海中的“弱”。
一种缓缓运转的古老意识不能容忍我,象巨大的油腻的齿轮上不能容忍一粒
沙子。
等待我的命运有两条:或者被清洗;或者被辗碎。
我的诗已上升为大地的旋律;它正逐渐伸入人、动物、植物的界线永久消失
的地方,极力去寻找潜伏在大地背後的古老的音韵。
在惯於备受“诗”赞扬自己的世界里,我的“诗”以牺牲一个世界的赞扬独
立自存。
“精神的原则是微弱的,它不具有暴力。”
“弱”是我的存在的真象和诗的情绪的哲学。
我出现以後,他说,是我把他从“停尸房”里抬到阳光下重新变成了一个“
活人”。
然而,我们的爱情也引起了一场灾难。在八三年至八四年那场全国范围内的
“反对精神污染”、“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中,他对我的爱情被公
安机关当成“流氓犯罪”。他们对他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牢,差点被处以极刑
,目的就是要彻底铲除他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使用了各种伎俩,希
望并要求我配合,承认是他的受害者。从一开始我就看清楚这是一场极为阴险的政
治迫害,如果我顶不住压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的话,他将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极刑
。由於我拒绝合作并严正抗议,加上他精通法律的弟弟黄杰多方呼吁,使得他们的
阴谋没有得逞。
在那次杀人如麻、可怕之极的运动中他能幸免於难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那是他第四次入狱。
八四年的最後几天,他被无辜关押半年後“无罪释放”,他理直气壮地要求
他们送他回去,说:“你们把我从哪里弄来就把我送回哪里去!”结果公安局局长
和政治处的处长亲自用车送他回家,到了家门口,他要公安人员亲自动手将他的行
李抱进家,公安人员也只好硬着头皮照办。局长伸出手来想与他握手,他傲慢地将
他的手推开,头也不回地进了家门,弄得那位局长大人万分尴尬。因为,他这次被
抓进去,当天夜里他们就提审他,这位局长大人一出现就恶狠狠地、咬牙切齿地对
他说:“黄翔!你这次进来就别想出去了!哼!枪毙你还差一点!”(那是因为我
没有屈服!)此刻,他又虚伪地向黄翔伸出手去……
在黄翔被“无罪释放”的头一天,我就成了“替罪羊”,在官方给学校施加
压力的情况下,校方召开大会对我进行了处分:勒令退学和开除团籍。我觉得很荒
唐,我的父母给我办转学他们不让,我申请退学退团他们又不同意,因为在公安机
关眼中我是块“肥肉”,不让我跑掉,现在他们的阴谋因为我没有得逞,就将气发
泄到我的头上,而校方又认为我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并且拒绝认错,处分我既“
正校风”又让公安机关下台。我毫不留念地离开了这所大学,可是,我被父亲“押
”回了郑州,离开贵阳时连与黄翔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正好女诗人唐亚平来看我,
只好托他送一块黄色围巾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给亲爱的黄翔留念。我连夜在围巾上
绣字,信没有写完天就亮了。我不知道这一别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亲爱的黄翔,真是
心如刀绞,失魂落魄。
我是八四年十二月三十号离开贵阳的。八五年元月四号,我就提了两包书跑
出了家,乘火车又回到了贵阳。我实在离不开我苦难深重的爱人,只有在内心乞求
父母的谅解和宽恕。虽然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爱情,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却受着爱情
和孝心的煎熬。我们终於冲破重重阻力生活在一起了,不久,我们“私奔”到他老
家湖南省桂东县,在那儿隐居了半年,那座在黄翔的《鹅卵石的回忆》中散发着忧
郁色彩的小小山城,真是令人难忘。我为那些碧清的湘水所触动,又取了个名字“
秋潇”,意为清澈的秋水,把它放在“雨兰”这个名字的前面,以纪念我们的爱情
。从此,我又多了一个名字:
“秋潇雨兰”。
在桂东隐居的日子里,他又听到那被毁掉的精神史诗在冥冥中重新响动的胎
音,他惊喜万分,原稿在他此次入狱後被毁掉,差点令他精神失常。我们赶回贵阳
家中的书房来分娩它,一九八五年的八月九日,新的精神史诗《世界 你的裸体和
你的隐体》诞生了。关於这部精神史诗,在卷首语中他是这样谈论的:
史诗的现代性就在於:
它不是编年史,而是世界的精神图象;
不是具体的叙事,而是抽象的抒情;
不是凝止的“块状”,而是流动的“片断”,
各自独立的片断构成全体的“整一性”,彼此相互贯穿为整体;
不是洋溢於表象的“热情”泛滥的语言,而是热情背後哲学语言的冷峻、凝
炼和简洁;
不是流於“现象”的歌颂、赞美、暴露、和诅咒,而是审视和超越万象的基
於诗情绪直觉的冥思与顿悟。
它的主人公不是看得见的“人”,而是消失得看不见的“精神”。
“诗是一部世界史、一部地球史、一部人类史,世世代代悉悉索索地翻卷着
。”
这是交给我翻动的一次。
我翻开世界的裸体和隐体。我发现:雕塑。岩石。浩瀚的力和运动。
阔。黑。空。
深黑的色调。潜伏的背景。岩石大地横蛮和笨重的语言的笔触。“自我本体
的精神的宇宙。”
这样,我塑出了我的痴像、呆像、露像、隐像、有像、无像。
追求一种个性的多面像的完成。追求散漫的回流於凝聚。追求诗的纷繁於简
洁。
尽管生活中常常阴云密布,多灾多难,然而,写作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无穷无
尽的乐趣,它使我们忘记尘世的痛苦,赋予我们一种神奇的力量,与厄运进行抗争
。继《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之後,黄翔又写了许多文论和诗歌,他明明知
道这些作品出版不了,但他决不会放下手中的笔。做他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听众,
我非常高兴,我喜欢听他讲解,也喜欢听他朗诵。能够面对面倾听他朗诵是很过瘾
的,他的朗诵具有非凡的魅力,他能点燃听众的心灵,使你随同他一起燃烧,一起
狂舞,一起爆炸,一起死亡和再生。
今天,我们又有幸目睹和倾听他的朗诵,《聂鲁达》这首诗写得棒极了,他
的朗诵也棒极了,政治的阴影被抛在脑後,每个人都被他发出的一种强大的磁力吸
引住,酒也忘记喝,菜也忘记吃,全身心走进他为我们创造的那片雄奇的诗的风景
……
屋外的光亮在渐渐暗淡,而屋内的情绪在不断高涨。除了朗诵声,一切显得
是那么安宁与详和。
小黄说不知跑哪儿玩去了。
院子里,小花坛上紫罗兰安安静静摇晃着绿油油的叶子,它们仿佛也在黄昏
里闲聊……□
|